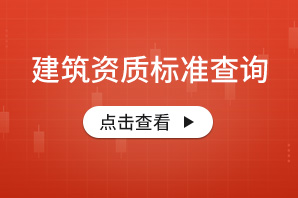-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
-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政策解读
- 强化电力监控安全防护体系,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支持电力领域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电力安全治理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政策解读
-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
- 挖掘数据要素 强化整合融通 推进城建档案信息资源一体化建设
- 国家能源局浙江监管办公室召开2024年度浙江电力调度交易与市场秩序厂网联席会议
- 政策支持新型储能加速发展 上市公司加码布局
- 我国建成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
深圳“农民农”现状:土地被层层转租蜗居危房
汲水淘米,劈柴煮饭,看炊烟袅袅,听蛙声阵阵,福永凤凰山脚、龙岗浪背村、石岩塘头社区等深圳关外地区仍有大量农田,菜农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只是在这里种田谋生的不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是外来务工的农民,又称“农民农”。
在对外宣传已无农民的深圳,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操着外地口音,时常满身泥泞,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也从未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任何红利的人群从何而来,将欲何往。
无农深圳外来农民种菜谋生
“农民农”概念是由“三农”专家曹锦清提出,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他们承租城市扩展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被闲置的农田,继续从事农业活动。因应城市化的发展,几乎各大城市都存在农民农这一新兴群体。
随着深圳城市化进程加快,30年来深圳从事农业生产的本地人越来越少,直至2004年深圳所有集体土地被收归国有,深圳再无户籍农民。不过,原特区关外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仍有大量农业用地存在。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委员会提供资料显示,深圳有10万亩农业用地,其中基本农田3万亩,而非法占有国有土地的农业用地情况尚无统计。由于存在有农田无农民的真空状态,引起外来务工者的注意,他们在深圳重拾旧业,成为城市中的农民。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就开始有了农民农,时至今日已有数万外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散布在原特区关外。深圳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农民早已完成华丽转身,不再种地而是“种楼”,坐收城市化带来的滚滚红利;而涌入的大量外来人口,大部分被各行各业所吸收,也有一部分外来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记者经过半年时间分别在龙岗、光明、宝安、龙华、坪山等地走访,对三百余户农民农家庭进行调查,作为生活在深圳最底层的群体之一,农民农群体身份尴尬处境艰难,没有任何保障及救助。
农民农多集中在关外。深圳的菜田除规划的基本农田用地外,多在水库旁、开发不充分区域,如福永屋山水库旁、龙岗浪背新村、光明迳口水库、民治民康路周边等地,一般有大片农田集中,数十至数百亩不等,而在南光高速、机荷高速、广深高速等地周边也有零星农田。农民农中以菜农居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多为广东、广西等地外来农民,绝大多数为租种,有少量自行开发者(私占国有储备用地),年龄集中在30-50岁之间。生产模式以家庭为主,多为夫妇二人并在此育有子女,同一菜田处多有同乡,文化层次极低,终日劳作,偶尔回乡,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几无业余活动。
农民农多生活在临时搭建窝棚,他们都面临着劳动强度大,生活艰难,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现状,绝大多数拖家带口在深圳艰难谋生,流动意愿较大,但选择空间小,如果遇到有更好机遇会选择离开。
处境艰难终日劳作收入微薄
来自茂名的张凯夫妇来深圳已有7年,两人通过老乡介绍在龙岗浪背村同乐蔬菜基地租种了两亩菜田。由于在老家就是务农为生,两人对种菜并不陌生,黄瓜、茄子、西红柿是他们常种蔬菜。张凯夫妇俩在深圳的第一年收入达到5万元,这在老家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担心孩子在老家无人照看,以及对老家教学质量的担忧,一年后将两个孩子从老家带来在深圳读书。
孩子到深圳后开销骤然提升,由于没有深圳户口,每个孩子每年学费及生活费将近1.5万元,而种菜成本逐年增加,两人逐渐入不敷出。去年张凯女儿病重,仅医药费就花去5万元,令两人多年辛劳尽付东流。如今一家人蜗居在租地公司提供的田边小房内,两口子思考着是否要离开深圳,毕竟在这里既无保障又看不到发展前景。
拖家带口在深圳谋生不易,张凯发出如此感叹。与老家相比,深圳的优势是蔬菜不愁市场,交通便捷,利润空间可观等,不过这些优势只是相对的,和深圳的其他行业相比,还是属于最底层,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每天凌晨3点起床,摘菜、拣选、捆上装车,5点前要运到菜市场,否则就只能两公婆跑到大街上叫卖,劳累一天不说,还可能血本无归。”菜市场里,从外部运来的蔬菜更有竞争力,“高产低价,本地蔬菜很难竞争。”实际上,本地蔬菜也有自身优势,就是价格灵活且菜质新鲜,附近同乐市场的摊主就较为喜欢本地蔬菜,只是需求量较为固定。
说到劳累,菜农的工作强度大得惊人。张凯夫妇二人早晨送完菜送孩子上学之后能得到片刻休息,稍稍调整后便要开始下田干活儿,施肥浇水锄草灭虫。如果正是蔬菜生长期,一般要干到晚上8、9点钟,之后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不足30平的阴仄小屋睡上一觉,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劳作。
“如果不是家中土地少,谋生困难,不一定会来到深圳。”张凯说,不知道自己做的决定是对是错,现在在深圳一样处境艰难。如果没有天灾,每月菜田收入有5000元左右,除去成本和生活费用,还要承担孩子的学费书本费等等,偶尔还要寄钱回老家给久病在身的老母亲,家徒四壁,生活清苦。张凯一家所住的是蔬菜基地提供的老式平房,与其他住户连栋,一排十余户,室内昏暗地势低洼,每逢大暴雨屋内轻则积水过膝,重则漫过床沿,没有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完全是原始农家的风格。30平方米的小屋被分割成卧室、厨房和储物间,显得拥挤杂乱。门外放着劈好的木柴和锅灶,便于每天生火做饭。平时几乎没有任何业余活动,有时遇到雨天无法干活会和邻居们喝酒聊天,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则稍稍丰富些,可以在田间赶蜻蜓,捉蝴蝶或是放风筝。
缺乏保障拖家带口蜗居危房
在龙岗浪背村同乐蔬菜基地,200户农民农家庭与张凯一家一样,这也是整个深圳农民农生活的缩影,拖家带口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在深圳没有社会保障及任何社会救助,房屋以危房乃至铁皮房为主,夏季高温闷热,冬季湿寒刺骨;每户菜农租种2-4亩菜田,四时供应周边菜市场,每家年收入2万-5万元。
对于农民农而言最怕天灾,一次台风或是暴雨,一个多月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每户菜农动辄损失数千元。
5月11日的暴雨,龙岗浪背村同乐菜篮子基地所有蔬菜均被大水冲毁,凤凰山脚下的菜田几乎被夷为平地,菜农面对满地狼藉的蔬菜欲哭无泪。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些习惯了,每年入汛总会遭遇一两场特大暴雨,无情地将他们数月的辛苦劳作带走。
今年四五月的两场暴雨几乎让本地蔬菜损失殆尽。本地菜农只能依靠老本度日,而其间多数农民农会到周边工厂打些零工聊以度日,但工厂对短工的需求量较小,所以只能做一些简单操作,工资待遇极低的手工作业,如缠线圈,嵌螺丝等等。
菜田相对集中,几乎每个菜篮子基地均有后天形成的“农民农社区”,在凤凰山下约500亩菜田旁生活着近千人,蜗居在一排排统一建起的逼仄潮湿的土房内。菜农称最烦夏季,多雨天气时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屋外雨停,屋内还是小雨。由于同乡居多,相互间感情比较融洽,有时会一起收菜卖菜,虽然生活艰苦,“社区居民”彼此也深知在此居住时间不会很长,但传统的生活方式及面对的共同问题还是让他们成为彼此依靠,平时遭遇疾病或是急事只能相互照应。
由于缺少保障并且无法落户,孩子在深圳只能读私立学校,而且每日放学要承担很大一部分家务,对学业也有很大影响,菜农更是忧心忡忡。“每年刨除房租水电,省吃俭用只剩下不到一万块,刚好给孩子做学费和生活费,这样还要牵扯一部分孩子的精力才能做到。”来自阳江的菜农董鑫坦言压力巨大,不知能坚守到什么时候:“想一边种菜一边打些零工,但不现实,打零工赚的钱少,还耗时耗力的。”问及遇到困难是否曾向当地政府部门求助,董鑫却说从来没有,“就是来种菜的,又没户口也没社保,求助能有什么用?”也有菜农表示曾因为菜田遭遇灾情希望街道部门给与帮助,但一直没有回应。
农民农虽然在深圳生活已久,但并未融入这个城市,仍保有农家最原始的状态,有些区域饮用水多为未处理过的地下水,需用木柴生火做饭。如凤凰山脚及浪背村附近,虽然与市中心不过十几公里的距离,但这里的农民农绝少融入其中,衣食住行都有难以解决的状况,在生存层面挣扎。
在深圳时间久了,老家人把他们当成深圳人,但是在深圳,即便是他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做深圳人,“迟早要走,种地是体力活,总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在这里种地,何况还是租的。”张凯解释道,“让孩子来主要是想让他们见见世面,多学点知识,将来考大学,找份稳定的工作。”张凯的愿望十分简单,但施行起来比较困难,对于他而言在深圳缺少选择空间,孩子的教育也受到诸多限制,没有户口只能上不知名的私立小学,学费高,教学质量堪忧,环境也仅比老家好一些,但孩子也会因为父母是农民而受到嘲笑。
隐患重重农药超标污水种菜
深圳农民农租种土地衍生出诸如农药的过度使用、污水种菜流入市场、超生现象泛滥等问题。而随着深圳种菜成本的上升,农民农群体的不稳定性以及去向均变得扑朔迷离。
民治民康路附近有二十亩左右菜田,因使用污水灌溉自2012年起屡见报端也未能解决。南都记者在该处走访了解到,该处污水来源为一排污渠,从龙华民治流至该处,菜农直接从污水渠中取水灌溉,让人观之欲呕。时值5月,排污渠水墨如汁散发阵阵恶臭,漂浮大量生活垃圾,很难想象用这样污水浇灌的蔬菜如何端上市民餐桌。当地办事处表示该菜地所在的地方是大龙华片区留下的唯一一个菜篮子工程。街道有意把该片区改成市政中心公园,但由于涉及修改土地用途,需要国土规划部门进行协调,整改一直没有推进。
除污水灌溉,还有农药的过度使用同样让人惊心。4月初南都记者在凤凰山下走访发现,一些菜农在使用农药除草除虫,一菜农向灌溉用水的井中连倒5瓶农药,然后进行喷洒,这些农药分别有除草、施肥、防虫、除虫等功效。该菜农表示并不清楚使用农药是否超标,但确实很有效果,能省掉不少劳力,有时自己也吃自产蔬菜。该菜农表示虽然农林水务部门偶有抽检,但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毕竟被抽到的可能性较小。而距离菜田仅一街之隔便是福永水缸之一的七沥水库,农药污染过的灌溉用水是否会汇入水库不得而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农民农群体并未落户深圳,且无户籍所在地的严格监管,超生现象泛滥。南都记者在农民农社区调查了解到,近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有超生情况,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家庭有3个以上的孩子。超生家庭负担沉重,也会给教育、医疗等方面增加压力,只是目前影响尚未显现,长此以往将会有大量黑户出现,足以引起警惕。
层层转租利润变少前途未卜
与污水灌溉、过度使用农药及超生等“显患”相对应的隐患是土地使用权责不明,层层转租现象严重,一旦遭遇旧改征地会引发群体事件。
为了改造建设基本农田,深圳市政府探索由市财政投资改造后,将基本农田承包给社区股份公司经营管理。据统计,此类交由社区经营的基本农田约9000亩。南都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到,社区经营的基本农田几乎都转租给外来务农人员,少有进行产业化经营的行为。此类农田转租现象严重,民康路附近菜田比较典型,菜农与承包公司深圳市寰通农产品有限公司所签订合同在2013年就已过期,公司已无续签意向,但时至今日菜农仍继续种菜,知情人士透露,该区域面临旧改,种菜农民期望从中得到一些补偿,而实际上作为租客,这种要求并不合理,但由于沟通不畅,数次险些酿成群体事件。
凤凰山下的500亩菜田租期同样于2013年7月就已到期。据官方资料显示,该处土地承包者亦为深圳市寰通农产品有限公司,而与该处菜农签订合同的公司则为深圳市联盛达市场管理公司,存在层层转租现象。菜农从2006年开始对基本农田附近的生态风景林区进行开垦,新开土地仍向联盛达公司缴租。从起初的百余亩已发展到500亩,且仍有继续开垦的迹象。根据菜农提供的合同显示,合同在2013年7月就已到期。南都记者与寰通公司取得联系,对方称暂时未与菜农续签合同,但不影响菜农继续耕作,只需继续交租。南都记者注意到,合同上几乎皆为对菜农的具体要求,并无一字关于菜农权益的保障。问及是否担心土地被征用后无菜田可用,当地菜农均表示走一步算一步,也有人称,在这种菜已有数年,利润越来越少,离开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实际上,存在利润变小就走的人大有人在,地租、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的提高,使得菜农口中上世纪90年代中至新世纪前5年“黄金十年”变成遥不可及的神话。以龙岗浪背村同乐蔬菜基地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地租每亩每年在600元左右,1998年调至750元,而后连年上涨,至2013年已涨至2020元/亩·年,菜价虽有上升,但利润空间却不大。“以前青瓜从田里送出去时是1元钱一斤,菜市场上近2元一斤,现在我们这出货差不多是1.3元,菜市场上卖3元,我们毛收入增加有限,但实际收入却变少了,再加上物价上涨,深圳已经没有什么太吸引我们的地方。”菜农张希在1994年从广西老家来深圳光明种植蔬菜,对于深圳农民农的生存空间有深刻理解,“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不过也有人想多赚点再走,但用什么方法去赚就很难说了。”
专家观点
保障菜农公共服务
监管菜农健康生产
2013年深圳本地蔬菜产量为10万吨,农民农所耕种菜田是供应的主力之一,保证了深圳人能够吃到本地的新鲜蔬菜。市人大代表杨勤认为,深圳的农民农同样为深圳的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们是深圳菜篮子的保证,虽然从事的是较为基础的行业,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深圳对于农民农问题的关注度确实不够,这与深圳历年来重视第二第三产业有关,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忽视农民农存在的理由。政府应该关注所有在深圳从事生产劳动的群体,不该太过泾渭分明。对于一些确实存在生活困难的农民农应给予帮助。同时菜篮子基地的品质也需要保证,对于菜农是否使用污水浇菜、是否过度使用农药都应加强监管,鼓励健康生产、环保成产,对于使用污水浇菜、过度使用农药者也要进行惩处,使得蔬菜生产能够更加规范化。
杨勤认为,外地人到深圳种菜,弥补的正是可能出现的菜篮子问题,可是现代城市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政府的相应政策似乎出现盲点,使这些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都缺少保障。从长期来看,这会导致部分外来农民离开,农田被闲置,从而直接造成农副产品供应短缺。
深圳市经贸信息委提供的资料显示,2013年深圳第一产业增加值仅为5.25亿元,深圳年产蔬菜10万吨、水果(荔枝、龙眼为主)3000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0.1%。杨勤认为,低端产业低端人群的存在不会影响深圳的核心价值,不过这与深圳自我标榜的“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宣传语相互龃龉,更与城市化文明相背离,不重要就不重视,是对人本价值观念的极度蔑视,不论你见是不见,数万农民农就挣扎在深圳的最底层,而由于农民农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进而产生的一系列隐患也需要面对,农民农何去何从不应该只是该群体自身的疑问。
●深圳农民农特征
来自周边来自茂名、湛江、阳江农民居多,亦有部分来自钦州、梧州、玉林
居住田边习惯居于田边小屋,以危房乃至铁皮房为主,租地的农民多为夫妻档,七成左右家庭有两个以上孩子
流动性大农民农会根据地租、交通、生活成本的变化选择租种点,有部分农民农因年纪渐大离开深圳
文化层次低九成以上为小学或以下文化水平
中年人居多年龄结构在30-55岁之间,年轻人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年老体衰者选择离开
形成新社区大块菜田由多户相对稳定的农民农聚居一处